走过百岁人生,吴良镛人民日报撰文:我的求索之路
- 汽车
- 2025-02-20 09:52:16
- 14

1993年,北京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工程被授予“世界人居奖”。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已走过百岁人生的我,1922年出生于古都金陵。
一个人的一生不能不思考到底想要做什么,立志是人一生不断前进的动力。而志向往往并非一蹴而就,是伴随成长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想一步步确立下来的。之所以选择建筑事业作为一生的追求方向,与我青少年时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我出生于国家内忧外患之际,祖国大地战火连连,苦难深重。1937年南京沦陷,我随家兄流亡重庆,于合川继续中学学业。记得1940年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合川遭遇日军空袭,大火一直燃烧至翌日清晨因降雨始息。战乱苦痛的经历激发了我重建家园的热望,最终选择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
以建筑为专业,这是一个开始。随着自己的成长,我对建筑事业发展的需求认识不断加深,学习兴趣也日益浓厚。
抗日战争期间,迁驻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一切都很简陋。当时建筑系的系馆是用毛竹捆绑的,瓦顶,篱笆墙。尽管如此,每个学生都有一块大图板,一张桌子,一只高脚绘图凳。窗外俯视嘉陵江,冬季江水清碧,春来垂柳成荫。系馆门口长了些灌木,每逢初夏,栀子花开,香气袭人……在那里,我度过两年半的时光。往事如烟,许多事回忆起来已若隔世,但有一件事至今未能忘怀。
一年暑假,系馆屋顶被暴风雨掀走,整修屋顶的工人原本歌声不断,但后来一位工人误触到高压线,不幸身亡,屋顶上顿时沉寂。
当时,我正读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感到分外凄戚。房屋、歌声、建筑工人,常常在心中串在一起,加深了我对建筑专业的情感,启迪了我的“人居”之梦。或许这就是懵懵懂懂的逐梦人生的开始。
1945年,参加了抗日远征军的我又回到重庆。当时意愿很单纯,就是要回去读书。在1943年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感觉开始对建筑学开窍,写了《释“阙”》一文,登载在班里办的《建筑》杂志上。回到重庆后,老学长卢绳找我,说梁思成先生希望我去见他。原来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看到了《释“阙”》,想找我谈谈。
梁先生学术视野开阔,走在时代的前面。这时期,梁先生已经开始考虑抗战胜利后的重建工作了。我到的时候,梁先生正在读沙里宁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他询问了中央大学的教学情况,又问我是不是对中国建筑有兴趣。我随感而发,说到过西南之后有所转变,战争破坏太厉害,想改为研究城市规划。
原以为梁先生只是谈谈话,没想到他明确让我留下来,当天中午就让我在那儿吃饭。后来我每天都去,工作了两个多月。当时,做的事情是为梁先生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进行完善。
后来,梁先生邀我去聚兴村看他。梁先生说他已获批在清华大学新办一个建筑系,梁先生希望我去当助教。我本来也模模糊糊地想走学术道路,这令我喜出望外,立即答应了,从此开始了在清华大学70多年的教学生涯。
在清华任教期间,梁先生推荐我去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学习建筑与城市规划,这是建筑师沙里宁创办的。
沙师的教导重在启发。他热爱东方艺术,说这是一个宝库,提醒我注意,不要失去东方的文化精神。匡溪的规定,学生毕业前,要举行个展。当地的报纸将我的展品作了报道,并列出沙师的评语:“在他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种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来自一般的人类文化发展,而且来自中国实际生活的发展,一种新与旧的结合,基于中国自身的坚定不移的精神。”
当时,我仅仅将其理解为一般的赞勉之辞,未加多想。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温旧事,回顾几十年来的道路,不就是在中与西、古与今矛盾中徘徊前进?!而什么是中国现代性的精神,如何能从中国实际的发展中发现、探索这种精神,时至今日,仍然是需要认真思考并严肃探讨的。
阔别祖国两年,收到一封林徽因口授、罗哲文代笔的信。大意是国内形势很好、百废待兴,赶紧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工作。在梁林两位先生的召唤下,我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从此开始一生为中国城乡建设奋斗的历程。
一个人的一生不知要走过多少“十字路口”,一个弯转错了就很难回到过去,因此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
回顾过往,有几次重要的“十字路口”。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留在美国,便没有此后几十年在中国建设领域的耕耘和收获。类似的情况一个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次。自我审视之所以没有“转错”大方向,还是与早年“立志”相关。我很早便立志在建筑与城市的学术领域做一些事,在不同时期,根据现实条件,做出相应的选择。
怀着心花怒放的心情,我积极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参与了长安街规划设计、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毛主席纪念堂规划设计等重大项目。
除了首都北京的规划建设,保定城市规划是我想特别讲一讲的。
保定自古即是“畿辅通衢之地”,在历史和地理上具有重要地位。开展规划工作时,保定旧城保存尚完整,也很繁荣,是居民的主要集中地。规划工作的任务之一是把旧城与跨过铁路即将发展的新区联结为一个整体。
我们对保定旧城保护、新区发展开展了全面规划,对道路、绿地等也进行了深入设计。规划方案不断调整,开始新区的道路网是斜向的,后来尊重当地的意见改为正南正北,最终形成了一个比较深入而实际的规划方案:东西城有机联结,有广场、有新中心、有绿带,空间有序、疏密有致,并且对旧城的大慈阁、南大街、直隶总督署、一亩泉等处的保护也非常关注。
在数十年的学术人生中,除北京外,我参与了不少地方的规划。但一个中等城市的规划得以较完整付诸实践的,唯有保定。
改革开放的洪流重新焕发了学术界的热情。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制度恢复后,我选上了学部委员。这使我有一种强大的学术使命感,获得了“建筑学要走向科学”的感悟。
创建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出版《广义建筑学》,完成菊儿胡同41号院工程,提出“人居环境科学”,主持撰写国际建协《北京宪章》,我主要的学术成果基本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之间的近20年间完成的,很值得怀念。
我为数有限的建筑创作实践多与文化遗产有关,菊儿胡同41号院工程比较有代表性。如何与环境保持一致?原则是“积极保护、整体创造”。
当时,41号院住了44户人家,但只有一个水龙头和街道公厕,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平方米左右,改建需求紧迫。
41号院的设计工作从1987年持续到1991年,十分用功。四合院的层数进行了突破,设计了2层、3层的四合院,在保证每一层都有合理日照的前提下,追求达到最高密度。楼房的四角安置楼梯,楼梯下方做开敞布局,使院落间能够形成通风。院子里原有的两棵古树也保留了,周边建筑都围绕这两棵古树布局。此外,在考虑多方面限制条件的基础上,在有限的用地面积上安置了最多的住户,而且每家都有自己的厨房与厕所。菊儿胡同经改造最终建成后,造价控制在每平方米500元以内,我至今还保存着单据。
第一期工程完工后,获得多方面好评,许多人认为菊儿胡同是“古都新貌”,旋即着手第二期改造工程。
1993年,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工程被授予“世界人居奖”,被认为“开创了在北京城中心进行城市更新的一种新的途径”。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建筑作品首次在国际上获取的最高荣誉。此后,我又陆续主持曲阜孔子研究院、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等的设计。
建筑当随时代,我们可以从多种途径发挥创造。作为一位中国建筑师,我深信,中国拥有深厚的建筑、风景园林和城市的文化传统,以及丰富的东方哲学思维与美学精神。如何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条件,吸取多元文化内涵,探索新的形式,创造优美的生活环境,这可能是避免世界文化趋同、促成当今城乡环境丰富多彩的途径之一。
时代需要“大科学”,也在孕育“大艺术”。2012年,因对人居环境科学的贡献,我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人居环境科学是随着改革开放,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的,涉及诸多学术领域,“人居之道”是科学、人文、艺术的融汇。
未来充满无限的生机和激情。作为一个建筑学人,毕生秉持“匠人营国”的精神,致力于“谋万家居”的事业,这是我的“求索之路”,也是矢志不移的“中国人居梦”。拙匠迈年,豪情未已,我对“明日之人居”充满期待!
(吴晨、郭璐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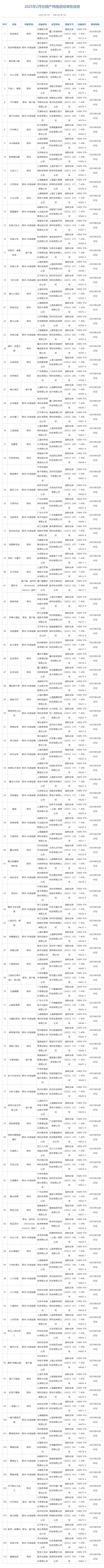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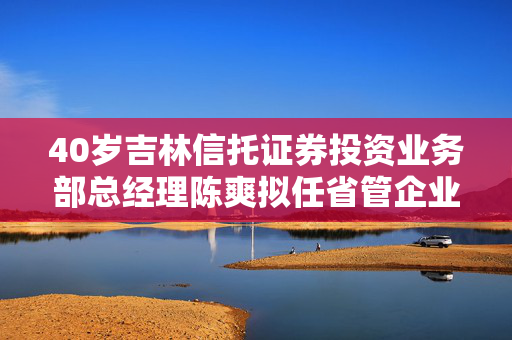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