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智丨新意·厚度·沾溉——读《西方新传记史学研究》
- 汽车
- 2025-02-14 15:04:07
- 37
世上无巧不成悉,
时时处处有惊喜。
一览史林多少事,
无不沾溉出新奇。
近读陈茂华新著《西方新传记史学研究》时,正是我重览西方古典史学的传记经典《凯撒历史回忆录》(现通译为《高卢战记》)之日,《经典是条河,经典是束光》的智音绵延“发掘与突破、修正与革新”的华声,于是新旧传记的理论探讨,在学术研究的长河中泛起几多涟漪,几朵浪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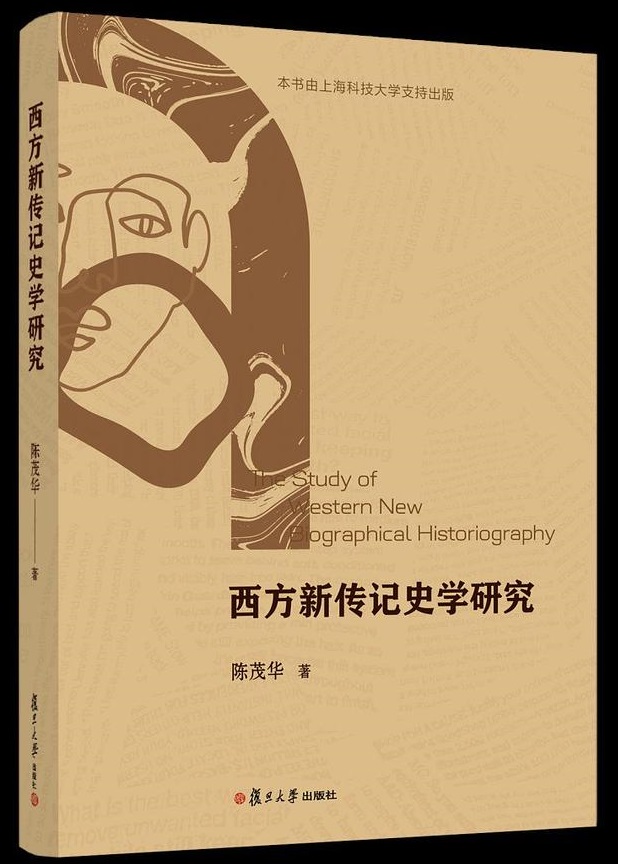
新意是学术命题的起跑点
即日,读到了葛兆光教授《第一等的题目和第一等的书》一文,他在文中指出,我们做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的人来说,第一个就是要有好的选题,“好的选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目标和理想,要敢于‘华山论剑’。”葛氏之言铮然。
《西方新传记史学研究》一书出版后,极速在学术朋友圈中传扬,好评不断,赞叹不已。本书选题新颖,颇具学术价值。西方史学理论学者、现旅居美国的陈新出言不凡,说道:“史学发展几千年,传记才是真正的主力军。”回望西方史学中的传记史可印证之。传记是两千年来历史学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一种题材或体裁。究其实质,传记不仅是一种讲述历史的方式,更是一种理解历史的方式。不言而喻,这凸显了《西方新传记史学研究》一书在选题方面的学术价值。历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本质上就是对人的活动之记录,而传记这一体裁正是通过个体的生命历程来展现时代变迁、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无论是古希腊被誉为“西方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还是自近代以降的世界各地刊出的绝大部分历史著述,人物始终居于历史叙述的核心地位。相较于宏观叙事,传记往往通过个体视角,讲述个人故事,使得历史变得更加具体、生动,而不仅仅表现为一系列抽象的事件或结构分析。众所周知,许多历史变革是由少数关键人物——帝王、将相、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等个体的决策和行动推动的。普鲁塔克和司马迁,之所以选择采用传记和纪传体的方式来书写历史,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关键人物——个体——的经历最能体现历史的演变。简言之,传记因聚焦于个人的生命体验而更容易让广大读者产生共鸣,更具可读性,更可能构筑文化新气象。在古罗马,凯撒的《高卢战记》甫一问世,遂成当时民众喜爱的读物,更成了近代学童的启蒙教本。行至19世纪,此书竟然在大仲马的长篇小说《基督山伯爵》中流传:小说描写盗首在深夜罗马城郊的陵墓里,聚精会神地在看他最爱读的《凯撒历史回忆录》(当时的译名)。
行至20世纪,传记史学亦历经坎坷而不绝,直到70年代的“叙事史复兴”。根据《西方新传记史学研究》的考察,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股史学新潮,汹涌澎湃,人物传记作为一种史学文体,获得国际史学界的广泛认可,欧美一些国家还专门成立了传记研究中心,与此同时,佳作纷出,比如美英两国新传记史学家书写的“无名氏”个体传记史学著作:劳雷尔·乌尔里奇的《一名助产士的故事》(1991年)、罗伯特·毕可思的《帝国形塑了我》(2004年)、沈艾娣的《梦醒子》(2005年)、玛莎·赫德的《船长的妻子》(2006年)、琳达·柯利的《她的世界史》(2007年)等。上书出版后,很快地为学界和广大读者所关注。本书以此五位“无名氏”的传记书写为个案,“试图在展现西方历史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自我更新之景观的同时,阐释新传记史学基于人性关怀的个体生命经验史观”(本书第6页)。其次,本书巧妙地利用结构安排来表现传主的多元化或类型化,从而阐明“一种以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为核心理念的多元融合的文明史观”(本书第49页)。作者在1月19号“思南文学之家”举办的“AI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传记”学术论坛上进一步指出,西方新传记史学的书写旨趣是对生命本身的关怀,实质上是一种生命传记(life writing),并非那种为了反对英雄史观(或伟人史观),转而简单、粗暴地倡导人民史观(或群众史观)。对此,本书颇有见地地指出:“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新史学与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根本性区分在于:新史学力主书写以具体的个人和特定的群体为主体的历史,而传统史学追求的则是书写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历史。书写人的历史,尤其是书写关于某一具体的个人和某一特定的群体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实则维持了历史知识对独特性、个体事件的研究兴趣,而非社会科学旨在对一般性或原则性的探究。换句话说,在新传记史学家的心目中,历史的意义存在于个别的事件,存在于具体的人物。新传记史学作为新史学的一个分支,它在理论视野上大大突破和超越了传统传记史学的研究框架,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平台;它在方法论层面上所展现出来的对某一特定历史主题的叙事策略,以及学科交叉特性和新史学分支整合性,是对史学思想的一种前沿探索,显然已经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历史分析工具。”(本书第57页)必须承认,作者通过对新传记史学个案的细致考察实现了对新史学思想的探究,并且,作者的这一洞见为理解和把握西方史学的演变趋势提供了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以“历史学的危机实质上乃是人类精神危机的表征”(本书第4页)为认识论前提,通过对西方新传记史学文本的细致梳理和整体考察,提出以下重要论点:西方新传记史学之“新”,更在于西方历史学家共同体勇于直面历史学在20世纪的艰难处境,敏于反思的能量,以书写自我史(Ego-Histoire)的实践方式推进历史学科的自我革新,试图重建历史学的学科正当性。而这一实践过程,实质上是历史学家自觉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投身于现代文化乃至现代文明的建设。也正是在自我史的议题这里,作者敏锐地意识到,有必要在史学史的研究范式之外引入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在这双重视域之中实现对西方新传记史学的整体考察。此外,在具体的、个案的考察过程中,由于认识到传统传记史学遵循的是一种“命题逻辑”,而新传记史学遵循的则是一种“问答逻辑”,因而作者同时采取了学术对话的方式来呈现和分析新传记史学的得与失。这均为本书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创新。
相比而言,现当代西方史学中,“传记转向”的潮流,较20世纪80年代萌发的“情感史学”“影视史学”等都要猛烈,可以这样认为,“新传记史学”站立在这股西方史学新潮的最前沿,彰显了历史学的人本主义特性及自我革新的自觉性。进言之,作者在“总论”中阐释了西方新传记史学的主要特征:强烈的反思性和综合性、多元融合的文明观、新时代的问题意识、注重历史知识生产的传递方式和叙事策略等,这些归纳贯穿全书,也是为本书“新意”一一作注,为其主题的旨趣营造地基。
总之,从凯撒的《高卢战记》到柯利的《她的世界史》,再到历史学家共同体的自我史书写实践,直至聚焦于身份认同理论的新群体传记史文本,传记史学历经2058年,真是“一览史林多少事,无不沾溉出新奇”。著者显然在新传记史学文本个案的研究、新旧传记史学异同的探讨,以及新传记史学与人生关系的考察等方面深耕,完全可以去“华山论剑”,勇于争锋。
厚度是学术命题的立足点
敢于“华山论剑”者,需要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兆光兄说要有资料和思考两方面的积累,要有沉着的气度和耐心,此言亦诚矣。就前者言,本书是一本厚实和宽宥的力作,且略说一二。
作者用丰赡的史料,酿就了新传记史学之腴。《西方新传记史学研究》是史学著作,上架建议亦是“历史学”,因此史料,特别是第一手的史料和原著,尤显重要。作者从西方新传记史学文本原著出发,不断打开一个又一个案例;研究西方新传记史学的“无名氏”个体传记书写、新名人个体传记、自我史和新群体传记等书写时,分别考察了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的个体传记、群体传记等等,这就为全书的宽厚奠定了殷实的基础。她在梳理西方史学传记史之时,自觉地在史学比较的视野下,着力阐释西方新传记史学是如何从认识论(包含价值观和道德观)、方法论(包含叙事美学)的维度去突破了传统“名人传记”史学模式,转向多元化、文化化、跨学科化及对话化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后者,即不仅表现为各种新史学之间的对话,而且还表现为与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人文学科的对话,从而得以彰显“历史学之性质、研究对象及意义:历史学是一门人性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有目的的行动,故而,研究历史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本书第59页)。纵览西方传记学史之长河,许多传统的传记作品不仅是历史记录,也包含丰富的文学、哲学及艺术思考,往往超越单纯的事实描述,着力于探讨命运、道德、权力等深刻主题。作者在西方新传记史学文本中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书写形式的延续,称其为“主题传记”,并由此切入而提出“传主时刻”这一概念,深入探讨了对于历史学而言十分重要的历史时间问题,以及新传记史学在此问题上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消解。又如,作者从新传记史学文本的书写策略入手,思虑历史学家与读者受众的社会文化语境,揭示西方现代社会的时代症候,意图从新史学的角度去阐明现代性的本质。以上所述,均反映出作者具有一种大文科的学术视野,胸怀一种“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的新人文主义观念。于此,亦可从作者在后记里引用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的那句至理名言——“人不是‘必朽者’,而是参与朝向不朽运动的存在者。” (本书第369页)——得到印证。
作者遵史论结合,赋予了新传记史学之萃。从文本切入,其思想精辟,其史论纵肆,它不是对传主生涯和风貌的简单排列,而是寻找目下的当代趣味以及深厚的时代内涵,特别是将历史学的学科危机处境和人类的现代性境遇结合在一起,在阐释历史学的特性之基础上,有理有据地阐述历史学革新的可行性及发展方向。新史学倡导从微观入手,意图得到“知微见著”之效果。然而,这一新史学思想的实践有时却避免不了“碎片化”的苛责。作者显然对此史学研究现状是了然于胸的,因而在考察西方新传记史学文本的过程中,她尤为留意呈现其在宏观、中观及微观层面上的历史叙事,并给予客观、中肯的评价,基本上实现了“知微见著”的另一重境界,即“臻于至善”。这一点在本书的第三章、第五章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此外,作者立足于当下世界的情势,在考察了西方新群体传记史学的研究现状之后,再度强调传记史学/历史学的人本主义特性。“在一个以大数据和算法为王的时代,我们人类应该如何思考进而构建自身的身份认同?毋庸置疑,这是一个要求从人本身出发来思考人的自我认知的重要问题。” (本书第367页)正是如此的史论结盟,不但使读者收获有历史知识,而且还有益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和审美认知的感悟力。
作者以“十年磨一剑”的气度和耐心,书写了新传记史学之魂。2013年11月,作者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读了芭芭拉·凯思的《传记与历史》(2010年出版),领略了西方传记史学的文脉,自此埋下了研究西方新传记的种子,后又于2017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功,于是她对这一命题做出了竭尽全力的探索,于2023年春以“优秀”等级结项,终成硕果于2024年12月出版。自2013年起步至今,用了十年多的时间磨亮了属于她的“宝剑”,现在终于可以出鞘了。
沾溉是学术命题的支撑点
“沾溉”,浇灌之义浸润之意也。提壶浇花几多载,沾溉新秀百花开。在这百花园中,茂华之新作是很亮丽的一朵,它从最初的含苞待放到现在的枝繁叶茂,母校、访学、实践,沾溉了她,最终在学林中点燃了史学之火。
岁月如梭,作者自2002年9月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攻博”,掐指算来,随我学习与研究西方史学史已足足有23年了。因为同城,师生切磋交流,问学不辍。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博士论文《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从答辩结束之后,经历了十年的不断修改出版,获得了学界的好评,随即成了她的“成名作”,也因此就拥有西方史学,尤其是近现代西方史学丰厚的知识储备与理论素养,为她写作《西方新传记史学研究》奠基。
说起茂华的“访学”,也是一个“无巧不成书”的“新奇”。《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的传主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教授,当她访学“哥大”时,霍氏早已成了过世半个世纪的先贤。但这位20世纪下半期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史家辐射到了这位中国年轻学者,她虔诚地“以一种真实的兴奋,不断地走近霍夫施塔特”,也就不断地对她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学术研究需要思想与实践融为一体,思想者不能闭门造车,墨守成规。在本书成书过程中,我特别欣赏的是作者的“团聚”学术活动。说的是她于2015年创办了“Muses”跨学科读书会,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友们,每逢周末晚上都在线上相聚,即使是抗疫三年间也从不间断,这成了他们砥砺前行和传递智慧的“学道”,这也滋养了“团主”的心灵,成了这一学术命题最有力的支撑点。
如今,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字人文的发展,历史学家可以利用大规模数据分析历史人物的通信、档案、社交网络,不断推动传记研究革新。我们可以预期,AI时代是一个“人人皆可书写自我史(或个人史)”的时代,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表达的那般,人们必定会更加关注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连接,会更加关注“生命政治伦理和责任问题”。作者在本书中指出:“相较于历史学家书写的自我史,非历史学专业的普通人书写的个人史,虽然也采取第一人称的视角和具有反思性质的自我叙述,但其主要以展现作为时代亲历者和见证者的具体而微的个体生命经验/体验为中心,并且意图将个体记忆融入集体/社会记忆之中,与本民族国家史或某个特定的群体史形成文本相互阐释的关系,从而实现对自我的认知和定位调整,以及对历史的创造——从个人的生命经验维度去定义历史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说,致力于书写个人史的普通人和书写自我史的历史学家的意图别无二致,二者均希冀通过彰显个人的自主能动的历史阐释权利,表达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及道德观,从而参与当下时代精神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建构。”(本书第301页)如今,国内已有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表达自我的重要性,他们正在满怀激情地利用多媒体叙述方式书写自身的个体传记。据作者在“思南文学之家”举办的“AI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传记”学术论坛上所述,本书甫一出版,即有不少正在书写个人传记的老年读者给作者发邮件讨要签名本,表示希望从书中获知书写个人传记具有何种社会价值以及如何书写个人传记的知识。作者指出,这正是一种实践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是她书写本书的一个初衷:有文化自觉,方有文化自信。换言之,本书的作者秉持的是中国的立场,始终关怀的是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幸哉,我中华!
概而论之,作者从悠长的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截取晚近三十余年的西方新传记史学,以揭橥它的文本与个案为基础,又与现当代西方新史学连绵,有别于旧传记史学的新面相问世,其论精辟意境深䆳,其文畅达布局有致,本书无愧为当代我国西方史学研究独树一帜的学术著作,亦为国人的中国传记史学和传记文学研究作参考,它将泽被学林,受惠于广大读者,至所盼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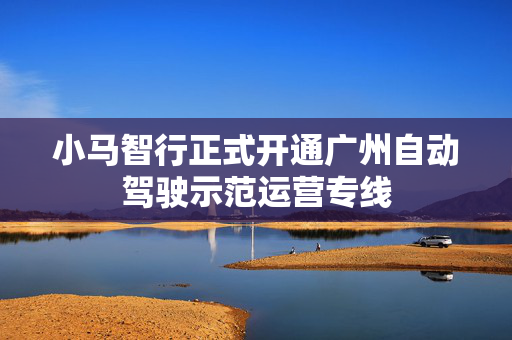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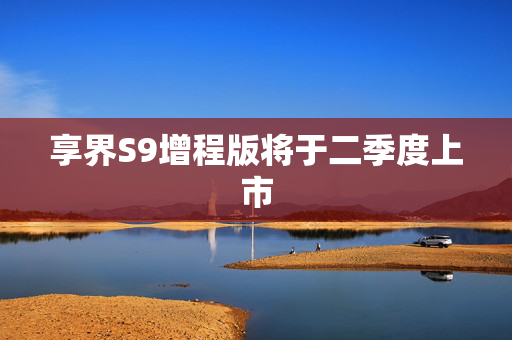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