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游》:语言的权力错位与影像的虚虚实实
- 创业
- 2025-02-11 13:50:08
- 11
2024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葡萄牙导演米格尔·戈麦斯接过了当年的最佳导演奖杯,这个曾靠着《一千零一夜》三部曲在戛纳大放异彩的鬼才导演,这次终于靠着这部独特的《壮游》入围戛纳主竞赛并一举拿下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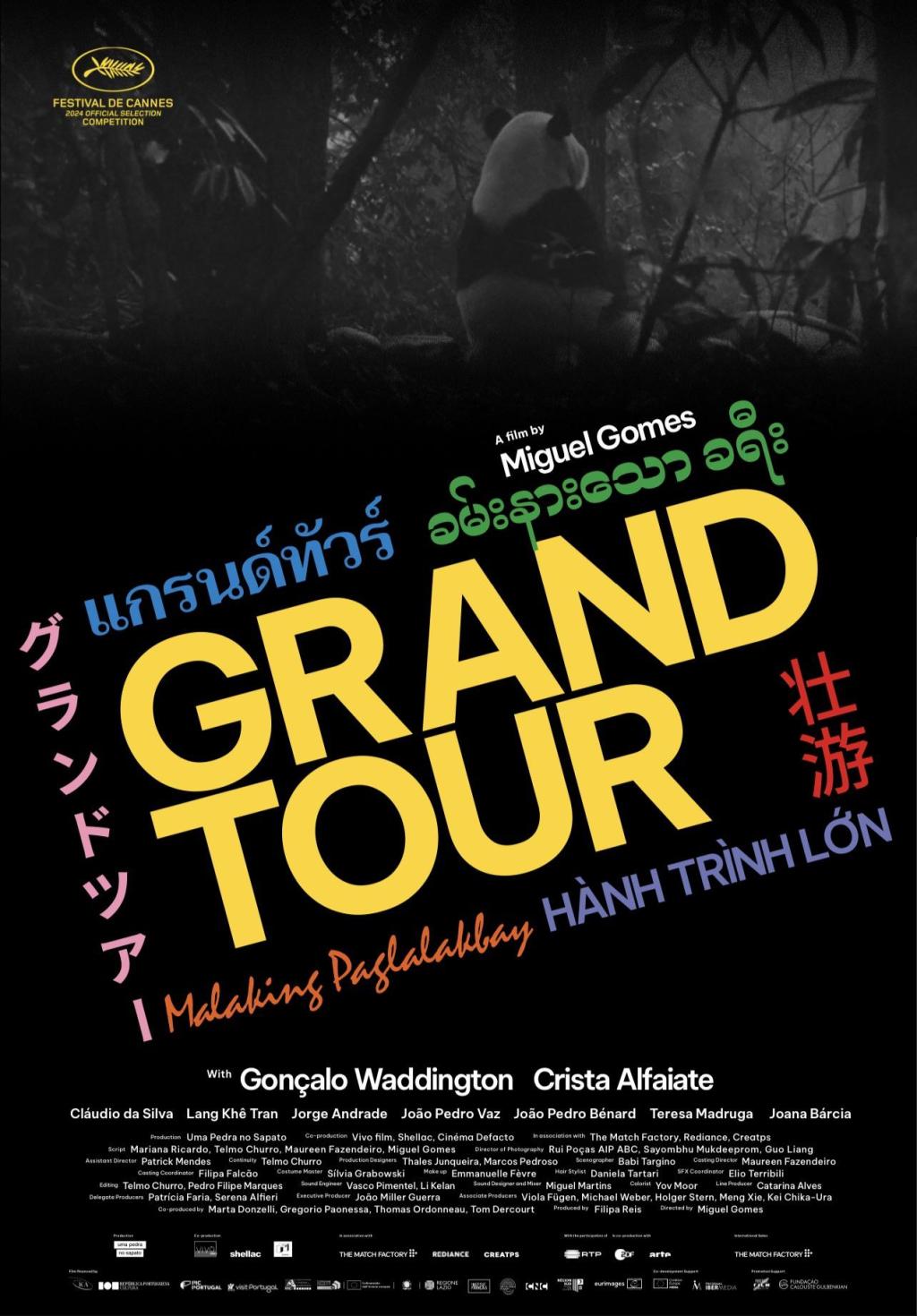
《壮游》海报
本片的独特设计堪称精妙,将一段迷人且富有东方主义色彩的故事搬上了银幕,黑白影像和本片多语种的旁白和台词所赋予的特殊质感给予了本片大量的解读空间。而在影像方面,导演将大量纪录影像和虚构故事有机结合,让20世纪初期的殖民地官员向东方的壮游旅途与21世纪的当下时空发生了连接。在一个穿梭于亚洲各大殖民地为背景的故事框架中,戈麦斯将电影的台词和语言脱离现实空间,还给原殖民地的居民,颠覆了殖民主义创作中的固有视角,构建了自己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开创出独属于他的叙事语言。
《壮游》的剧情其实十分简单,故事改编自毛姆小说《客厅里的绅士》中仅仅只有两三页的内容。一名叫爱德华的大英帝国殖民地官员想要逃避面对自己的未婚妻莫莉于是横穿亚洲,而莫莉为了追逐他紧随其后。懦弱而恐惧婚姻的爱德华和强势的莫莉前后从缅甸的仰光开启自己的旅程,途径新加坡、曼谷、马尼拉、大阪、上海等等最后坐船到重庆再进入藏区。
剧情而言,这仿佛又是一部视觉化的、背负着殖民者叙事逻辑的电影,无论是在当今影坛,还是回望过去的电影,带有此类奇观性质的西方视角电影都并不新鲜。比如改编自凡尔纳同名小说的电影《环游地球八十天》,成龙在其中以中国人的身份替代了原著中“路路通”这一角色,从而使得电影的剧情可以在原著的基础上发生改变,主角一行人也得以进入中国大陆并开展一系列精彩冒险。商业电影在对殖民主义著作的改编上无法跳脱出原有的僵化视角,而其商业化的本质也使得导演和编剧在重组文本时,需要考虑到演员以及消费市场的关系。
这仿佛传递出一个非常悲观的信息,即在当下这个距离“帝国”和“殖民”等名词如此遥远的新时代,影像这个曾象征着先锋和当代意向的表达形式,依然很难重塑原有的文化认识和世界观。

《壮游》剧照
而当我们对影像叙事中既有的、且不断重复的世界框架和单一认知而感到厌倦时,戈麦斯通过《壮游》呈现出了一副非常独特的画面。首先值得表明的是,《壮游》不能被盛赞为一部反对殖民主义的旗手电影。米格尔·戈麦斯在本片中塑造的的叙事手段依然没有直面殖民地,以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在占据本片几乎一半篇幅的非纪录镜头中,故事的演变也只是顺从历史的框架和电影中架空的人物关系。
但值得一提的是,戈麦斯在台词和影像处理上对《壮游》所展开的堪称实验性的改编,使得这部电影在剧情故事之外也存在重新诠释的空间。
语言的权力错位
无论是从后殖民理论视角下作品的解读出发,还是针对单一作品的理解,话语权都是电影中最重要的构成,它是决定这个作品所呈现角度和代入视角最直观的权力象征。殖民主义惯例和叙事方式常常将被殖民者塑造成“野蛮、落后或被需要拯救的形象”,对于电影而言,电影所主要选用的语言也依然是话语权的直接体现之一,正如在现实世界中,勒令被殖民者学习殖民者的语言是一种巩固统治的殖民工具,电影中的语言也是反映作品以及创作者文化属性的一部分。

《壮游》剧照
但在电影《壮游》中,戈麦斯将电影中的语言权(也是话语权)还给了讲述者本身。当电影的两位主角在壮游中抵达亚洲的各个城市时,电影中大量城市的空镜搭配着叙述者的旁白填充了电影中转场的部分。有趣的是,本片作为一部所有主角均说葡萄牙语的电影,旁白却都使用了当地语言,多语种的旁白朗诵了那些没有被镜头所拍摄出的爱德华的遭遇,通过这种文学性的方式让“壮游”这一电影的母题加以延伸。于是观众得以听到缅甸语、泰语、日文,直至我们最熟悉的中文。导演似乎有意用这种方式向我们表明,这并不是一部只服务于单一群体的电影。
而正如上文所述,本片的所有主角都奇幻般地说葡萄牙语,但是在全片故事框架中,爱德华以及其妻子都属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人员,英国官员竟说葡萄牙语这种错位,在本片的语境中就无法被解释为一种拍摄事故或是低级错误,反而是这种刻意的“错位”同样是戈麦斯构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部分。
在这部架空的故事中,缅甸、泰国等这些在帝国时代遭受过殖民的前殖民地都在电影中精确地获得了自己的话语权,而英国、葡萄牙这两个原殖民大国却都在这个故事中搅浑了自己语言和文化的联系。殖民者的语言被边缘化、模糊化,被殖民者却拥有着自己独立且明晰的文化和语言。语言所反映的权力关系在本片中发生了颠倒,这种语言上的权力错位正是戈麦斯所想要去反思并最终呈现的。
影像的独特风格——虚假与真实
而在语言之外,影像的独特风格也是《壮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片的主线剧情围绕着爱德华以及其妻子的游历展开,但呈现这些画面时电影只使用了室内置景,这些风格独特的片段都在搭建的摄影棚中拍摄,而用于转场的画面则是均由城市空镜组成。别具一格的是,这些城市的镜头并非是符合20世纪初殖民时代的城市旧日景象,而是大量使用了当代纪录影像作为填充。

《壮游》
这些画面均拍摄于故事中角色所处的城市,因而所有的影像呈现了这些前殖民地区域近两年的人文和地理风貌,这种差异让摄影棚中所拍摄的那些虚假的20世纪初画面和现当代的真实影像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影片中虚假的摄影棚拍摄画面漏洞百出,比如进入中国的藏区时,路上遇到的所有行人均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些并非无意之举,《电影手册》称其是“于2023年以一种1930年代好莱坞式的异域影像风格,在摄影棚内被复现”,这种在过往的电影中就频繁出现的西方人对东方文化(也可以被理解为被殖民者的文化)的高傲也被戈麦斯精准地复刻。
从文化属性上而言,影片的剧情片部分也是印证了了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描绘过的“西方对东方的学术、文化和政治话语,它不仅是一种学术领域,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工具。”在电影的文本上,戈麦斯也借在藏区路上遇到的老头,对男主说道:“白人完全无法理解东方文化,这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这更是直接将这种“蓄意的复刻”直白地表达了出来。
本片通过调用不同的影像和不同性质的画面的组合,其所刻意塑造出的抽离感仿佛也在印证了殖民者对“他者”的文化剥夺,而戈麦斯则是将虚幻与真实高度统一,形成了他自己独有的看待世界的方法。除去拍摄的剧情部分,导演对真实的纪录片影像部分的处理也让真实和虚构、历史与当下的界限变得模糊和错乱。当爱德华从曼谷的皇宫逃往西贡的路途中时,描绘曼谷与西贡的纪录片影像出现了大量的叠加和虚化。值得一提的是,在片中,剧情部分均为黑白画面,但纪录影像则是插入了各种颜色,这种手法使得两部分影像在美学上无法高度达到统一,似乎是有意让观众在画面处理手法的差异上逐渐认识历史与当下,甚至去分辨虚构与真实。
这种影像上的混淆直至结尾才被分离干净,电影结尾莫莉在寻找未婚夫爱德华无果,最终在藏区无力地倒在地上时,镜头拉远,剧组的探照灯出现、剧组人员出现时,电影似乎终于打破了那最后一面“影像和观众阻隔的墙”,让剧情片部分在观众眼里彻底沦为“虚构”的代言词,在电影的结尾精妙地埋下了一个对电影艺术本身探讨的种子。
如果说将语言的主体还给被殖民者,是语言所象征着的权力错位,那将呈现影像的权力还给他人,则是标志着将表达的权力下放给了所有能举起摄影机的人。
壮游的文化属性
《壮游》所肩负起的文化属性是鲜明而锐利的。在一个后殖民时代,在摄影棚中按照过时的、东方主义的视角所拍摄的殖民时期的壮游旅程,搭配上当代的纪录影像以及多元的各个语种旁白。在影像上还是语言上都显示出戈麦斯对过往的“殖民主义认知”或是“东方主义认知”的叙述甚至是反击,对历史片的解构和重组形成了这部看似各种元素高度对立,但实则价值体系保持统一、拥有独特质感电影。
《壮游》绝非一部旗帜鲜明地表现出反对殖民主义的电影,这种判断主要是基于戈麦斯在本片中所选择的两套叙事语言和影像模式,戈麦斯也通过影像传递出两套叙事逻辑。
在人为拍摄的剧情部分,爱德华和未婚妻无论前往哪个国家、面对不同角色,都以葡萄牙语沟通。即便在故事中,二人的身份应该是英国人,但这里使用的语言究竟是葡萄牙语还是英语已无足轻重,重点是语言被殖民者牢牢掌握着。同样地,正如前文所点出的漏洞一样,各个国家的剧情拍摄也充满着对当地人民的刻板印象,沦落为背景板的人物也不过是由简陋的文化符号填充组成,使得这一切都仿佛一出拙劣的舞台剧。

《壮游》剧照
而这种粗制滥造,以及对语言和台词的控制正是戈麦斯想要传递出的质感,这一部分的正是对应着殖民主义作品中的霸权叙事。这标志着语言在殖民时代往往是充满垄断性质的。混杂的语言被粗暴地搅乱,被殖民者语言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被悉数绞杀,而殖民者的语言则变成了体现文化优越性的工具。或许这样的设计之下,这种叙事手段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警醒,在21世纪重塑一出充斥着殖民者傲慢的戏剧和文化输出依然是一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或者说我们将其他民族视为“异端”和“他者”的排除异己行为依然也是一个需要时刻警惕的“滑落”。
当电影中的纪录影像呈现出来之后,和剧情部分又形成了鲜明对比。该部分对原殖民地区域的表现又充分展示了其多元性和现代性。而搭配着这些纪录影像的旁白,用其多语种的声音向我们展示了西方视角中的“东方国家与民族”的复杂性。我们大可以将纪录影像这部分理解成后殖民主义文学的一次抵抗。这两部分形成的对比也刻意加强了后殖民时代中多元的话语权。彩色的纪录影像与黑白的剧情影像形成对比;单语种的葡萄牙语与多语种旁白形成对比;虚构的历史影像与真实的当下影像形成对比。戈麦斯在电影中用影像穿插的方式使得殖民主义作品和后殖民主义作品在这一部《壮游》中达到了共存。
值得讨论的一点是,在《壮游》中大量出现的,具有本土性质的戏剧在文化属性上究竟又代表着什么。在大段的纪录影像后总是紧跟着实拍的该国本土戏剧,这个极具文化符号的片段却似乎依旧无法展示出后殖民主义作品对被殖民者文化和语言的正确认知。在剧情进入上海这一部分时,纪录影像展示着上海外滩和陆家嘴的现代景象,而后却搭配着略显违和的少林寺功夫。这一突兀的行径似乎也是一种西方对东方的偏见和简陋认识,对东方的再现也只是将概念化的文化认知加以揉杂。
这种设计绝非刻意为之,而使得电影和创作者本身变成了他们想要传递的价值观中的一部分。《壮游》用精妙的视听语言构建了一个独属于电影的“殖民主义、东方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文本。尽管殖民时代与帝国时代已过去百年有余,在一个更为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当下,突破殖民时代留下的那充斥着傲慢与粗陋的文化认知究竟还有多远,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像手持摄影机的人不断的迭代那样,只有当表达的权力下放到一代又一代之后才能明晰。
文献参考:
李昌银. 霸权与颠覆——英国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殖民话语研究[J]. 金田,2014(7):92-93.
澎湃新闻.专访|戈麦斯:重要的是让观众能以私人的方式和电影产生连接
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移居者的隐喻》
文学报.2021诺奖解读:古尔纳融合作家与评论家身份,反思殖民历史与移民问题
《电影手册》.《轮舞》:米格尔·戈麦斯的壮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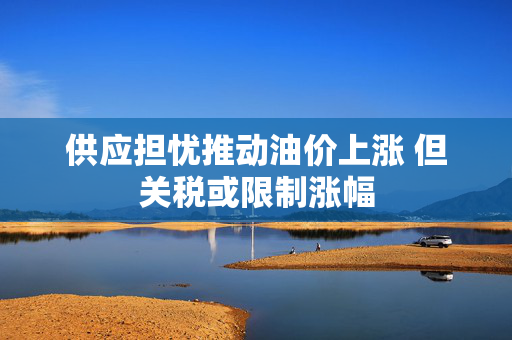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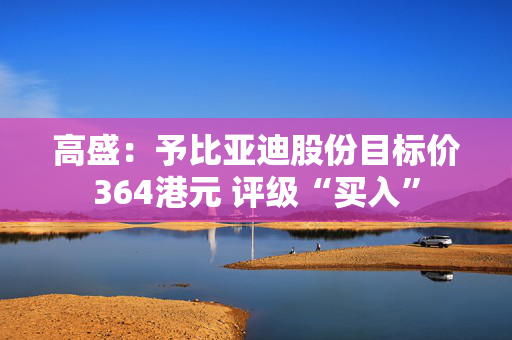









有话要说...